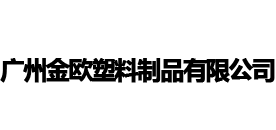邓伦知道,人生的主题之一,或许就是解开纠结和纯粹之间的矛盾。现在他敢于把「我喜欢不喜欢」作为选择的最高标准,还想要把握更多的主动权。「最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,你要活自己的人生,还是给别人看的人生」
《夜旅人》中邓伦有场在医院的独角戏,没有台词,但要用身形表现出“非常、非常失落”的状态。他也知道,这场戏剪到正片里最多两三秒,但拍完后看回放,他就是觉得“不对”。
导演都看出他那天有点儿“丧”,说如果哪里有问题,要不重来一个?每个演员都有状态不够好的时刻,能做的只有调整自己,邓伦于是默默消化掉心里的这份不适宜。这算不上什么大状况,要是心大一些,过去就过去了。但它们却变成了细细的针尖,在邓伦身体里刺出密密的不安和焦躁。
身为演员,在现场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导演的要求,邓伦当然知道,自己的判断和最终的镜头呈现之间会有出入,剪辑、后期等等效果都会校正表演的完成度,“被动性”从来都是这份职业的属性。“有太多东西演员控制不了。如果事后说起现场的那些遗憾,我可能会说要放过自己,但当时当刻可以放过吗?我很难做到。”
知道客观的限制,他就要在主观上尽可能地给到多一些。“对,演员只能负责演戏,但我们不得已在乎,因为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全部奉献。演员对自己的要求不是100%,而是120%。”
观众在观赏成片的时候,或许压根都不会注意到那一晃而过的几秒,但邓伦觉得所有的纠结有其必要性。“因为我知道剧本,我知道人物,我知道那几秒有多重要。其实我们不仅是表演给观众看的,更是拍给自己看的。这事儿马虎不得——甭管剧本最终如何、硬件是否尽如人意,接了你就要尽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好。有要求的演员,都会有点儿钻牛角尖吧。”
之前,拍打戏时为了表现最佳的肌肉状态,他硬是忍着尽量少喝水。我问他,值不值?观众或许体察不到银幕上肌肉线条那一点儿微妙的区别,但他却需要实实在在克服生理的困难。邓伦的回答几乎不带犹豫,值得。“演员心里要有一种纯粹的东西,不能有太多预期。你不能去问导演和剪辑,能不能给我剪个肌肉特别美的效果?要不能,我这就去喝水了。”
他能把握的、会尽力把握的,只有当下。他也经历过糟糕的结果:在剧组待了很久,结果上映时自己的镜头一个都没有,费心费力拍的作品,上映时间遥遥无期。“过程中我钻过的牛角尖、我对一场戏状态的不满等等这些观众更不会知道。但别人同样不知道邓伦在拍摄这部戏过程中的成长,我可以把这些积累放到下一部戏,那时观众可能会发现,哎,好像邓伦又有些不一样了。”
到现在,拍每一部戏、每一场戏前,邓伦还是会感到紧张。他曾请教过许多同行,也询问过不少前辈,让他欣慰的是,绝大部分的人都告诉他,生出这种感觉是对的。“有些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,有人甚至已经斩获过许多个影帝,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紧张。这不是一种惧怕,而是一种对自己的高要求,但紧张是好事,它会让你更专注、更集中。”
表演当然需要技巧,但现在技巧对他而言更多在于和镜头的配合,而不是放在感受或是和对手戏演员的互动上。以前他还会事先做点设计,这儿怎么演、怎么走,现在他的大部分感受都随心而来。每拍一部戏,他都想尝试一种不同的表演方法,“我也在寻找哪种表演方法是最对自己最合适的。”
这次,因为要在电视剧《夜旅人》中扮演律师盛清让,在拍摄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,邓伦都穿着西装三件套,“永远全副武装”。穿这种制式的服装,是否应该有一种更挺拔的体态?他还真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。
“西装加上领带,自然会给你一种束缚感,但我个人的理解是,在束缚的同时,它又是向往自由的,而不是真的把你’框’起来。”他参考了包括《教父》在内的不少经典影视作品,“即使他们是绅士或是贵族,平常交谈的姿态也是非常随意的,很张扬。”
进入一个人物最直接的方式,就是先把外形做到极致,但要从微不可察的细节中渗透人物的背景和性格,这需要长久和细致的功课,所有看得见的人物表象,邓伦都会尽可能地去抓准。
盛清让出生于望族,旅法归国后是上海滩的名仕,相比大多数同年代的人,他理应更时髦和前卫,从发型到装扮,开机前他和导演都有过仔细的讨论。他甚至有点儿担心,最终的形象观众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,和他们对以往“民国公子”的印象不一样,“但我还是想保留那个年代最为原本的东西,而不是完全去顺应现在的审美。”
每次开机前,读剧本都是让他最感兴奋的环节,“你能够最终靠文字去想象、扩充许多画面和空间。”这回,他和扮演女主角宗瑛的倪妮都提前一周进组,围读剧本,“虽然不是真实在演,但我们会先梳理出一个共同的方向,但是也会保留一些未知给现场。”
从读文本走入实体的置景里,身临其境总会给他更多意想不到的感触。“除了色彩、气氛之外,能让你更切实地体会到人物之间的关系。当所有演员从纸上的描写变成真实的人物站在你面前时,当他们把各自对角色的理解转变成释放给你的能量时,当他们同样在吸收你的给予时,会彼此激发更多戏剧的灵感:哦,原来我在你心中是这样的,哦,原来故事最终要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方向。”
即使准备得再充分,拍摄现场总会出现些意外:有时是天气,有时是演员的身体状态,有时大家能将错就错,有时却只能硬着头皮扛过去,但“不在掌控”的情况,邓伦遇见的少之又少。充分的准备之外,他也感激这次主创团队的工作方式,“就是大家把一切都聊舒服了、准确了才开始拍。即使出现一些小状况,它们也不会变成阻碍。”
邓伦很喜欢《夜旅人》的故事,这是他用足够的耐心等来的结果。他认定,演戏不是一两天或是一两部作品就能定论的事情,在不同的阶段,可急也可缓。之前他差不多有两年没有拍戏,“我没觉得有太大的问题,可能明天突然碰到好些出色的剧本,我一连拍三四部也不稀奇。”
但在旁人看来,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,正值盛年,创作力和体力都在巅峰状态,这样长时间的等待,似乎有些可惜。既然没有一个角色会成为终点,为什么他不可以一直在路上,边走边试?“但我没有很好的方法放低一点儿自己的标准,就是我不想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妥协。”有些工作对他来说是锦上添花,接了也挺好,不接也没所谓,“没有感觉的事情”上,他不想做无谓的消耗。
但演戏不可以妥协。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成长。一部戏到最后,口碑如何、市场如何,这些都不是我能左右的部分。也有人找我,说这戏你来就一定怎么着,但我不想做全部为他人服务的东西。我想多学习、多充电,没拍戏的这些时间里,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家人,也录制了一些不同的节目,都是在换一种不同的体验,让自己有更丰富的感触。”
作为个体,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客观,在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,他干脆就把“我喜不喜欢”当作最高的衡量标准。“我这个人是这样的,只有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,我才可能把它做好。我不太能勉强自己,不然只是达成目标。我不想欺骗自己,更不想欺骗观众,压力当然有,自己扛着就好。”
他说的“自己”,也包括身边的团队。在他屡屡推掉戏约的时候,团队也要同他一起承受质疑,甚至为难。“有太多的东西会压过来,确实很难。其实我往往也不太能说服大家,我也知道这样可能有点儿为难,但我拧不过心里最真实的想法,我可能并不太能get到那些故事本身。”
有时他也问自己,我是否有点儿不讲道理?“确实有点儿。但回到我自己’喜不喜欢’的角度,我又觉得挺讲道理的。”他庆幸团队和他之间在这点上可以达成互相理解的默契,“他们了解,就算我去了,效果甚至还行,我心里还是整个别别扭扭的。”何况,谁说以后没机会了?“不是说我之后不拍戏了,也不是说未来再也遇不到(好的项目)了,不至于。有些时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极端,给自己留些缝隙。”
这种坚持其实有点儿理想主义。身边的人或许能够理解,但更多人会以“为你好”的名义劝他“该如何”,越过所有善意,回到初衷,他常常会陷入“两难”的境地。
“我清楚自己喜欢什么,也清楚自己不喜欢什么,但我总是做不到,或者说,做选择的时候我还是更多去考虑别人的想法。我常想,可能自己暂时有点委屈,但让大家都舒服,反馈过来自己也会更舒服些。”这让他在做事的过程中更多了一份自觉的责任,“有些事对你来说可能无伤大雅,对别人可能是件正事儿,那你要为别人负责啊,就不能光想着自己喜不喜欢。任何事情都在不停地转换。”
长远的目标,邓伦心里很清晰。“我也想将来获得一些重要的表演类奖项,可以再拍几部特别好的作品,每个演员都抱有这样的希望。但不能因为这样的希望存在,你就盲目地往前奔,不是你拍越多的戏就会有越多的机会,或者能拿更多的奖,我不想目的性那么明确。希望一直要放在心里,到落到现实的时候,还是要一点儿、一点儿把自己给凿实了再往前走。”
欲速则不达。他想,人生的主题之一,或许就是解开纠结和纯粹之间的矛盾。“我对自己还是有个简单清晰的规划的,人生还长着呢,在这个年纪,能体验一下自我也挺好。”
邓伦第一次去录制综艺《极限挑战》的理由,是因为他没试过那样的节目。第二年节目组找他的时候,他只问了一个问题,“那几个哥哥都来吗?他们来我就来。”
雷佳音是他上戏的师兄,两人之前一起合作过电视剧《白鹿原》,于工作于生活,一起经历了不少事儿,情分扎扎实实摆在那儿。两人每次见面,邓伦都有点儿小感慨,世界一直在变,彼此都还是当初认识时的样子。在雷佳音看来,《极限挑战》里的这群兄弟总能有意无意把他从某种极端的情绪里拽出来,哥儿几个开开心心一起“历险”的记录,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节目的所有外在目的。
邓伦也有同感,“我们一直在聊,就是收工后的内容要是也能拍下来,那又是一个节目了。”他觉得和这几个人彼此间有点儿特别的缘分,能凑在一起,是种幸运。“我们也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但彼此非常了解,又知道怎么互相迁就,所以每个人都特别、特别珍惜这段友情。”他参与的第一年,录制最后一期的毕业典礼时,他和雷佳音都哭了,几乎从没在公众场合落泪的郭京飞也哭了。
回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各自冷静了一下,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。“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,我们为什么要哭?谁都没想通,不就是录个节目吗?大家都没想到会投入那么多的真情实感在里面,可确实是真心换真心啊。我觉得这是拍戏之外,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段经历。”
录制《密室大逃脱》,是因为他喜欢“研究逻辑性的东西”,不过这也让他对自己有些意外的发现,“说实话,录这个节目前我不知道自己那么怕黑。”小时候他总是跟着一群大孩子出游,在家附近的老旧建筑里“探险”,那里虽然一样充满了未知,但害怕的感觉似乎不能相提并论。
“我都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法一个人待在那种黑暗里……不过我也没想到大家会觉得这样好玩,还以为大家会和我一样感到害怕。”或许是每次都太过投入,他压根没意识到主观视角和第三视角的本质不同,“不过我也没有任何的包袱,我录任何节目都只是做自己,整个沉浸进去。录制《密室大逃脱》的时候,我根本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艺人,我就是个玩家。”
他喜欢这个节目的真实感:没有开工收工的时间,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和事先对接细节,“最多有人告诉你今天穿这件衣服,下楼,上车,然后就把你往密室里一扔,再见。”虽然屏幕上他的所有真实反应都会被围观和讨论,甚至被up主剪辑在一起,多了点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,他也觉得没关系,“就放飞自我呗。”
邓伦甚至打算自己开一间密室,自己最喜欢的东西,他就想尽可能多分享给别人一些,“最好大家都能来亲身体验。”从玩家转换成设计者,他又打开了另一扇新世界的大门,“其实设计密室和拍电影有异曲同工的地方,你也需要置景、道具、演员,也需要故事。此外还需要加入很多高科技的东西,比如机关、音效、灯光这些系统,但它又没有影视剧那么高的资产金额的投入……”
说着说着,邓伦似乎暂时陷入了一种创业者的愁苦。“这其实是一个入门门槛挺低的行业,但你又要把它设计成精品,要让参与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,又不能修片、剪辑、调色,不能后期加配音,站在那儿,零距离的体验就是当下。”
但凡是有兴趣的事情,邓伦就会花心思主动张罗。他希望自己能更多表达对于主动权的要求,而不是被动等待别人的安排。“如果你表达得不够明确,别人也会疑惑,你到底想不想做?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意愿。”
被人知道目标没什么不好意思的,即使看来现在还需要些时间和机遇,他觉得不妨说出来。“比如,不管多少年之后,我一定、一定会自己做一次导演。会不会成我不知道,但至少我会体验一次。”
生活的节奏,他也想自己把控。这几年他花了许多时间来陪伴家人,“好像慢慢长大,会发现很多事情在倒计时。小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些,以前也有过两三年不着家的那种,一直在剧组玩命拍戏。现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晚,而且我能分清什么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,你不能光想着自己,家人和朋友才是你人生中永恒的东西。”
有人为邓伦操心热度、曝光、发展,但把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上,他看到自己的收获,是渴望平常心。“就是对每一件事都不会那么急功近利,我在调整,希望工作或是生活都能更平常一些,不要为某件事变得太极端。”如果要排序,工作在他心里的确只能放在第二位,“最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,你要活自己的人生,还是给别人看的人生?”
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,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,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。
联系电话
13826200057 宋小姐电子邮箱
jinousuliao@163.comCopyright © 2020-2020 安博体育游戏官网登录下载 版权所有 粤ICP备2020122305号 网站地图